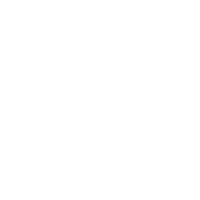中国基督教两会唯一的官方杂志《天风》至少发表过三篇直接写到周联华牧师的文章,如:2015 年第 12 期(总第 432 期),篇名:《“我要活得好像没有明天!”——走近传奇人物周联华牧师》;2017 年第 2 期,篇名:《周联华牧师对本色化神学的贡献》;2023 年第 12 期,篇名:《牧者心 中国心——当周联华牧师面对“洋教”的责难时》等,可见周牧师在中国基督教界是举足轻重的。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周牧师的见证。
第二部分:周联华牧师在台湾的境遇
在外界看来周联华牧师是“总统牧师”,一定会很荣耀、很舒服,其实不然。由于周联华牧师的身份,他在在台湾基督教政教关系上倒是显得错综复杂。他作为“世界圣经联合公会”干事,曾为中国大陆教会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印刷机 T32 印机,并争取到数千吨的“圣经纸”,也曾联合港台地区和内地展开联合翻译圣经工作。此外,他还在两岸基督教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 2012 年 12 月访问过北京基督教会,2015 年参加了“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 100 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并曾邀请中国基督教两会组团访问台湾,因此他被台湾当局某些人贴上了“红色”的标签,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和注意。
周牧师始终都与长老教会的人士有着紧密的友谊,长老教会1972年发表的第一份宣言,其最开始的起草人即是他。实际上,周联华可以说是台湾基督教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教内有不少基要派分子(基要派也称为基要主义,是一个神学分类,而非以组织形式存在的独立宗教派别)想给他找麻烦,所幸他都能全身而退,其中的矛盾和冲突难以避免,但是由于他身上有诸多的“光环”等原因,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奈何不了他。
1988年中国台湾所谓“国安局”公布的“黑名单”中,惊见周联华的名字刊于其中。在台湾外界总以“总统牧师”来称呼周联华牧师,主要是他负责凯歌堂主日讲道,蒋介石与宋美龄是基督徒,也都是他讲道的对象,后来蒋氏父子两代的追思礼拜也都由他主持,外界基本上都认为他是一位政治牧师或应该是与台湾当局关系不错的。然而,这一切观感都可以说是极其表面的,很少有人知道周被列入“政治黑名单”以及种种陷他于囹圈的指控。据台媒介绍:周牧师甚至因为无法删除这些台湾当局为他设立的黑档案而最终听从宋美龄之劝,只得留在台湾、留在凯歌堂,可谓“最危险的地方,即是最安全的地方”,或者是“就近看管”,反倒可以让外界没有太多做文章的机会。
事实上,中国台湾地区“警备总部”早已盯上周联华牧师,怀疑他的种种行为,并检查他的邮件和窃听他的电话,甚至还调查他过去曾在中国大陆做过什么。根据1964年6月19日台湾省警务处至警备总部文提及这些事:“至于周联华其人,本处有其涉嫌数据,在对普案处理的意见,经常以代表身份申请出境,赴国外各地参加普世教会协进会各种会议者,处列为核心分子侦监,并开始检查其邮电。
周在就读沪江大学……曾参加演出左倾作者巴金之《家》。
周联华透过陈纪彝(蒋夫人之同学)之关系,而得以经常参加总纪官邸凯歌堂之礼拜。对于此等WCC核心分子钻营掩蔽之活动能力,颇为识者殷忧。”
以上是台湾地区“警备总部”档案所记载的,可见周牧师的处境。
据有学者介绍:台湾省“情治单位”把周牧师的底细挖得非常的清楚,根据他早年在大陆大学时期参加过的活动,包括表演话剧剧本的“左倾”,以及他响应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广泛阵线,推动国统区群众斗争与军事行动形成合力,参加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推断他与“共匪”有过接触。他们罗列了周牧师参加普世教协的活动记录:1962年日内瓦普世教协总部演讲,1963年3月出席由普世教协在东京召开的国际事务委员会,1963年7月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并于会中进行报告。不仅如此,台当局甚至对周师母阮郇瑶女士也列为监视对象。
周联华牧师是一位在国际有影响的基督教牧者,曾四次与基督教界重要的位置失之交臂,都与他被台湾地区粗暴的政治上的干涉和“敏感身份”有关,他形容自己为“恒久的候选人”。外界都以为,贵为“总统牧师”,其在基督教界的地位应是一帆风顺的,至台湾少浸信会神学院院长一职应不成问题。原来董事会已经通过确定由周牧师接任院长之职,却忽然变卦,神学院内部有人酝酿起“倒周运动”,表面上是信仰不正确,事实上,更关键的是“政治不正确”。老院长柯理培把周牧师叫到办公室,要他写“信仰告白”,以解外界之惑,周牧师不从,认为“信仰告白”只对上帝而非对人说的。柯院长退让一步,好言相劝要周牧师不要与长老教会、天主教往来,周牧师坚定的回答:你们可以决定我不当院长,但不能决定我与谁交朋友,况且,长老教会和天主教都是我的弟兄姐妹。
说完这番话周牧师就气冲冲地走出院长室,正好巧遇张光直的小女儿(张光直先生是首位将中国考古学系统引入国际学术体系的学者。他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后赴哈佛大学深造并获人类学博士学位。他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并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等职,他开创性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更是少数在西方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华裔学者),这位小朋友用一如往常见到周牧师时表现出的童稚的话说:老朋友啊,给我讲一个故事吧。顿时,他的怒气烟消云散。(周联华:《我的一生》,台北,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09-122页。)
台湾当局的“幕后代理人”,对他的“亲共”行为指证历历,而且在台湾基督教教会界人士也经常基于“维护纯正信仰”和“维护圣经权威”的立场,暗指周牧师的神学或信仰甚至是对待圣经的态度都是“成问题”的,这些人大都是“护教”的主要干部,事实上,周牧师也同样地卷入了基要派对他的圣经翻译的“新派”思想的攻击。
因为负责凯歌堂的工作,外界都把周联华说成是“总统牧师”或“蒋家三代的牧师”,实际上也就是如此。但讽刺的是台湾地区“警备总部”有一大批关于他的“黑档案”、“黑材料”。事实上,蒋介石和宋美龄都知道那批档案和材料,曾经有人想对他下手,但蒋和宋没有发话,是没有人敢动的;许多与他互动的国民党高层都知道这些事,只是没有人可以做出改变。周联华曾为帮助黄彰辉(黄彰辉Shoki Coe,1914-1988是台湾长老教会的重要领袖、神学教育家,也是推动台湾本土化神学与自决运动的关键人物)取得出国签证而暗访党政高层,他甚至为台湾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被捕之事做过努力,这些都是他认为在那关键的时刻该做的事,当然这些总不免成了人们大做文章的可能,尤其他自己也“深陷囹圄”,随时都可能“下落不明”。据说还有一位浸信会的神学生曾差一点被收买,要给周牧师加上一些罪名,结果并未成功。
周联华牧师公开且得意地提到他有份起草《国是声明》,特别是第一段文字,全是他的意思。他不仅是在政治正确上,尤其是在信仰正确上,经常成为别有用心人的攻击目标,基要派对他的攻击从未少过,台湾省“护教反共”以来的诸多争议性事件,都看到他的身影在其中。周联华牧师与长老教会互动密切人尽皆知,但因他在凯歌堂与蒋介石、宋美龄的近距离关系又使反对他的人又顾及,而不易、不敢下手。所以在“党国基督徒”的眼中,周牧师在“反共”上不够用力,在护教问题上多次违反“纯正信仰”的立场,他多次被人质疑他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包括参加普世教协的活动、接受天主教为教内分子、所谓的、莫须有的罪名,如、经翻译的神学错误、本色化神学主张的“谬误”等等,每一项罪状都足以让他在当时的台湾当局“政治正确”上被控告,所幸他总是可以安全地走过来,个中的复杂因素肯定无人能解。不管如何,周牧师就不属于“党国基督徒”那种褊狭神学立场的人,再加上他的政治立场更是在他的神学底色中难以回避其政治上倾向于“自由派”,而且,所幸他安全地活过了那个年代,所以才可以通过他的回忆录去重现历史的现象,无疑地,周牧师绝对是一位传奇般的人物。
所以,蒋介石与宋美龄虽然口头上说对他被列于黑名单上是了解的,但在那种年代里,尤其是贵为“总统”身边的牧师,且与长老教会及与蒋有介蒂的人士(如何应钦、张学良)互动过密,很难不成为被看管的对象之一。留在凯歌堂,当然也不失为有“就近看管”的好处。
一位台湾省的牧师这样说:周联华牧师在台湾就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耳朵所听见的那样,在一个政治对生命充满着威胁的年代更是如此,若不是上帝的保守,周牧师都不可能全身而退,他的存活堪称奇迹,要不然,他的尸骨恐怕都找不到。正是这样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就发生在周联华一生的遭遇中。
在这里我们介绍周联华牧师的政教关系著名之作:《另一位见证人》。
1975年蒋介石逝世,在台湾岛内引起巨大的骚动,基督教界中曾经有不少人写文章来吹捧蒋,比如《黑纱》。这也引起无数人的期待,希望“总统牧师”周联华牧师也可以写一本类似于《黑纱》的书来追忆、吹捧蒋,或者有人认为周联华牧师怎么能有理由不写呢,何况可以将目的放在“传福音“”,借助一位“伟人”的形象,“传福音”肯定会更有效。
以被形容作“总统牧师”的周联华牧师如此密切与蒋的互动,看来是最有资格、最理所当然写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生活和其人格等方面的。1976年4月,周联华牧师终于出版了一本名叫《另一位见证人》的书,封面是一张蒋介石坐在书桌上阅读圣经的照片,书的内页还是周牧师自己用笔写下书名和自己的名字。大概是经过刻意的包装,道声出版社的编排、设计夹带了许多照片,加插在书的内文中,绝大部分都是蒋介石出殡的一些照片。全书共六章,目录如下:
第1章 总统安眠的卧室;第2章 总统的信主经过;第3章 总统的灵性生活;第4章 信仰行动的合一;第5章 大人物的小故事;第6章 总统的神学思想。
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本书竟丝毫没有留下任何给人去崇拜蒋介石或神化蒋介石的机会。在他的文章中成功地避免了“造神运动”。也许,外界那些“党国基督徒”或一般热心信徒,都期待周联华牧师可以藉此机会宣传基督教,公开蒋的宗教生活无地疑是给人予以崇拜他的理由。但这一些读者的心理期待都在这本书中被拒绝了。《另一位见证人》给人近乎无从挑衅的理由,即在于全书很难找到对蒋近乎神格化的文字描述,周牧师果然是一位“读过神学”的神学家,是位有智慧的牧师。
首先即是书名,这是一个与基督教的信仰原则和立场相合宜的标题。从标题上已清楚说明,蒋只不过是众多见证人的“其中一位”而已,所以他是“另一位”;而且,蒋也不过是普遍一般的“见证人”,不是什“伟人”,与其他所有的基督徒身份是一样的,都只不过是“见证人”,是诸多的见证人“之一”,无须有任何特殊之对待。
《另一位见证人》从内容来看,周联华牧师更是处处表现得小心翼翼,全书并有六章,前两章都是在说蒋夫人宋美龄如何、如何地提到关于蒋的种种,另外三章都说一些极其琐碎、无趣的事,包括蒋介石的卧室、睡过的床、凯歌堂礼拜的题目或内容,还有令人更觉意外的是,说到了讲话的口音、小白狗、金鱼、敬酒、吃油条等等无关紧要的琐事。
周联华牧师大约是1954年开始到凯歌堂讲道的,他主要接触的是蒋宋美龄,更多的活动场合是在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真正担任凯歌堂的牧师始于1966年。周牧师的一段话说明了他在凯歌堂如何地低调:“每一位参加崇拜的信徒都是追随总统和夫人数十年的袍泽或部属,皆是寻常的聚会,自然地专心崇拜。在凯歌堂我所面对的会众,总令人深深体会到他们每一位在对国家的贡献和对领袖的效忠上,都是一个整体。在这整个会众中,如拿世俗的眼光来看,最疏远的应该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了。”(周联华:《另一位见证人》,台北:道声出版社,1975年初版,第63页。)
尽管有这么多的机会接触蒋介石,周联华牧师在《另一位见证人》中唯一用直接口吻形容蒋的印象,就是他的鼻子、眼睛、口型,正如周牧师所说的:“我在凯歌堂讲道21年,我没有害怕过。与其说是我没有害怕,倒不如说总统没有使我害怕,我是像在其他教会完全一样的讲道。”所以他没有去塑造蒋的神秘和伟大,自然也就不留下人们对他过分崇拜的理由。也许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最后一章:“总统的神学思想”,看来这章可是一次借此吹捧蒋的思想伟大的机会,不过,周联华牧师竟然“聪明地”只是大段大段地摘录或抄写下蒋介石的一些语词,不做太多的解释,像是将蒋的言论进行分类,有关本色化、宗教与科学、精神与物质、善与恶、信仰与行动等等,尤其说明是由“夫人抄录”交给他的,这就使得别有用心的人不敢造次。
在台湾省那个狂热的拥蒋年代里,《另一位见证人》可以说是一本最为“清醒之作”,他没有参与“护教反共”的狂热,也没有丧失信仰判断地神格化蒋,留给读者做文章的机会,尽管他是最有资格把蒋的信仰人格神化的人。这似乎应验了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曾庆豹:《黑名单上的总统牧师——周联华与台湾与台湾基督教的政教关系》)周联华牧师善用了他与蒋介石如此贴近的距离,任何人想要从他那里要他做些什么事,都会触及到、冒犯到蒋,也许是这样,这些人也不太敢对周有太多的要求或期待,所以周在蒋的身边反而是安全的,但他并没有滥用他的机会,这一切都说明周牧师是一位踏踏实实受过神学教育的人,是一位忠于信仰的基督徒。
从这本书并未引起“党国基督徒的”大肆吹捧来看,《另一位见证人》是周联华牧师的失败之作,无疑的,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它代表了那个年代还有如此清醒表现的基督徒。《另一位见证人》这本书,同样是在政教关系的主题上突出了其意义,重点就在于,有没有好好学过神学确实是有差别的。
据说,冠世远牧师曾被人诬告他是“共匪”,理由是他在大陆时期参加过共产党。当人问及周联华牧师对此事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即使他是,那又怎样?”这又是一句极富智慧的话,堵住了所有想用此理由陷害他人之举,也为寇世远牧师提供了庇护。
周联华牧师一生饱受基要派分子的攻击,都与他主张的合一运动有关:与WCC的友善关系、1965年百年大会、1966年与天主教联合祈祷会、1970年倡议与天主教出版共同译本(2015年终于推出了《四福音书》“共同译本”,超过半个世纪的等待);80岁后仍频繁赴大陆讲学、赠经;2008年代表联合圣经公会向金陵协和神学院赠送希腊文与希伯来文原版圣经;2010年访问青岛教会并证道;任台湾世界展望会董事长十余年,推动“饥饿三十”“资助儿童计划”;担任南京爱德印刷副董事长,协助印制上亿册中文圣经……这些都被扣以“新派”(背道)之名。所以有台湾学者写到:“所幸,周牧师都能全身而退,实为不幸中的大幸,多少人在此之中深陷囹圄,像台湾信义会的金仲庵那样的可怕遭遇,至今想起都会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2016年8月6日,95岁高龄的周牧师下山途中突发心脏病,逝于振兴医院。按其遗愿,入殓、追思礼拜皆从简,不挂遗像、不收奠仪,以诗歌敬拜代替歌功颂德。他一生“奉派作传道、作使徒、作教师”,被誉为“台湾现代基督教史缩影”;其学生遍布全球华人教会,其译本与著作继续塑造无数信徒的灵命与思维。他主张唯爱主义,反对以牙还牙,强调“不争辩、不吵架,宁愿退一步,以基督的爱赢得对话”。周联华牧师以学者之深度、牧者之温度、译者之广度、公益领袖之力度,在政界与民间、堂会与学院、本土与普世之间搭起桥梁,成为20世纪华人教会“公共信仰与学术神学结合”的典范。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全文完。)